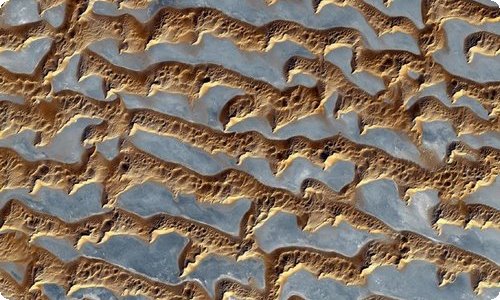姐大如母散文
大姐在家中七兄妹中排行老二,小大哥三岁。在七兄妹中大姐最勤奋,用任劳任怨这个词一点也不为过。19岁前在家中就是个大劳力,拉纤、撑船、装卸货,样样在先。在“文革”的年代,作为党员的父亲一年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县城参加各种会议、学习班,大哥16岁就参加了工作,安排做轮船的驾驶,家中所有的生活自然就落在了大姐身上。
家里最早是15.5吨的小木船,通常装砖头、黄砂、石子以及百货,除百货以外的货物基本上都由自家来负责装卸,十多岁的大姐一个人能挑起一百多斤的砖头担子行走在狭窄的跳板上。二姐负责码砖头,大姐负责挑上挑下,姐妹俩不到一天的功夫就能将一船的货物装卸完毕。有一年夏天发大水,堆在河边的砖头被淹到了水中,货主出工钱让我家下河去将砖头摸上来,被浸泡在水中的砖头可能是平常砖头的二三倍重,大姐和二姐俩人摸了一天一夜,工钱拿到手的时候尽管已疲惫不堪,但在那个近乎贫困的年代还是有着不小的成就感。两个姐姐没有上过学堂,不知精神为何物,但这种成就感却足以丰富她们单纯的内心世界了。
子女多的人家总是事多,大的哭小的喊,这些都算是常事,家人在一起的日子里总是喜忧参半,艰苦的生活被迫着要为生计而努力,比我大十岁的大哥只上了三年级,15岁时就参加了工作,父亲常年在外的时间多,小妹还没出世,二哥在学校读书,家中就三个姐姐和我,他们在行船的时候我就被笼头套着。有一次二哥放假在家,大姐在切罗卜的时候他伸手去拿,一不小心被大姐刚落下来的菜刀切断了一根指头,还剩下一点皮连着。大姐的惊叫声和二哥的哭喊声乱成一团,闻讯起来的妈妈赶紧用布把二哥的断指包起来,据说过了没多长时间二哥的指头就长好了,最终都没落下残疾。
二哥断指的事件中,大姐是无意的,她在家庭中年长于其他弟妹们,因而她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也大于其他弟妹。大姐的脚板沿着里下河地区的所有河道,背着纤板,一步一个脚印,一步步地丈量着年轻而枯燥的青春旅程,将花一样的年华消耗在大丰的斗龙河畔、卯酉河畔,直到16岁上升为劳力开始拿工分,从这时候起她便有了一点点的收入。但在父母身边还得靠这一点的收入来供养我们小弟妹3个。到了19岁时大姐面临着两种选择:上妇女船队;去水上二村务农。父母坚持她去水上二村。
接到通知时,家里的船已去了镇江,趁着装卸货的空闲,大姐揣着平时买菜省下来仅有的5块钱上街上购置了些必备的物品,面盆一只,茶缸一只,还买了一个工艺品,一块只有8寸大的正方形刺绣,上面是2只活泼可爱的猫眯,至今还挂在妈妈的老房子中。
水上二村是单位在乡镇购买的一块几千亩土地,所有人员都是由单位调配过去的,除上升劳力一部分必去锻炼外,其他都是些单位富余劳力,说得不好听就是单位的劳改农场,几千亩的土地由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开垦变成了良田。大姐去的时候就是开河沟、长棉花、种水稻,大集体上工,计工分,集体化管理,听到钟声上工、放工,食堂伙食,自己购买饭菜票,宿舍是一人一小间,房屋是单墙加草顶,窗子是纸糊的,条件极其简陋,几十名上升劳力,他们没有条件进学校读书,为了能早早减轻父母的负担走上工作岗位,自食其力,挣得自己一份少得可怜的收入,到了婚嫁年龄为自己操办简易的婚礼,就算是安家立业了。
大姐去水上二村不足一个月,突然有一天有人把最小的妹妹送到了她的身边,大姐在日后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常常苦笑着,称小妹妹是被人邮寄到水上二村的。大姐不在船上,我和三姐上学了,小妹妹在船上少了人照应自然很不安全,父母只好狠狠心托人将小妹交给大姐照应。既成事实,容不得大姐讲条件,五岁的小妹妹很懂事,眼里只认得大姐。大姐上班就哄着小妹:
“宝宝乖,你一个人在家,饿了有吃的,你自己吃,自己在家里玩,困了就上床睡一会,等姐姐回来啊。”
妹妹很乖巧,一个人呆在家里目送着大姐上班,然后就隔着门窗每天盼望着大姐身影早点出现。大姐放了工一点也不敢耽误,待到她打开门的时候时常会看到已伏在桌子、凳子上睡着了的小妹,有时嘴里还含着没吃完的零食,然后大姐会小声地叫醒她,帮她洗脸、洗手,然后做饭给小妹吃。跟大姐在一起的时间就是小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碰巧天气不能上工时大姐也会抽空带小妹走访其他工友,大伯一家也在水上二村,有时大妈还会喊她们去吃上一顿。
最恐怖的是夜幕降临的时候,不大的村庄之外到处是阴森森的灵火在游走,妹妹问:
“大姐,那是什么啊,我怕!”
“不怕,宝宝乖,那是人家打的灯笼。”大姐把小妹紧紧地抱在怀里,赶紧帮她洗了上床,哄着小妹入睡。
小妹在的日子里大姐是余不下来钱的,但逢有人进城,大姐就会请人带些小吃给小妹,请人买来布,然后自己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帮小妹缝补衣服,再苦也不会委屈了小妹。
大姐是个碰到活计就会往死里做的人,她的工分总是比别人多,吃的苦也是最多,没有因为要带小妹而影响自己的劳动,有她在二村的日子没人在劳动上能赶得上她,她用自己拚命的劳动来赢得大家的尊重,小妹也由此会沾上一点光彩,加上小妹的小嘴也甜,在那个大家庭式的半农半工的集体生活中也成了大家宠爱的娃娃。
大姐和小妹在二村的日子里,我被爷爷遗弃在马房。我上小学三年级,照例放学回家远远望着马房上空晚饭时光的炊烟,但当我兴匆匆地回到爷爷居住的马房时,却突然发现不见了爷爷的身影,室内已是人去楼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一屋的东西只剩下我几件堆在墙角边的破衣服。后来人家爷爷奶奶跑过来告诉我:爷爷跟三叔叔回盐城定居了,从此我就一个人生活了。
两年后我小学毕业,我转到了单位办的水上学校上初中,大姐结束了两年多水上二村的农民生活回到城里,被安排在船厂造水泥船。离城较近了,日子要比在二村好了许多。小妹一直跟着大姐,没多久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近在水上学校读小学。
我在上了三年的中学之后转眼就到了1980年,大姐到了婚嫁的年龄。这年底大姐被大姐夫用扎着大红花的自行车拖着回到船厂分的一间宿舍,从此大姐就有了自己人生中的另一个家。一直跟着大姐的小妹看着大姐坐上了大姐夫的车,非常着急地问道:我怎么走啊,我坐哪儿啊?一大家的人看着她一脸的幼稚神情和焦急的样子都逗笑不已。
一年后大姐生了个女儿。
船厂,原来是以船舶修造为主,先是造些小型水泥船,不久便开始造钢质船舶了,大姐也是第一批电焊工,有造船任务时就造船,没造船任务时就修船,用电焊对船舶进行缝缝补补,也就在那个时候大姐学会了抽烟,有电焊技术的人在那个年代是吃香的,人家都要求助于大师傅帮帮忙,需要缝缝补补的铁器都得求助于她,经不住船主们的好意,也就慢慢叼起了香烟。叼着香烟的女工在别人眼中一定是个大师傅,大姐也是尽量满足别人的求助,同时也要注意以不损坏集体利益为原则。
对家人方面,家庭中的大事、小事最先到场的也是大姐,她在我们家庭中充当着老大的角色,处处为家人着想,事事得体,在对待弟弟妹妹方面就充分显示出她大姐的身份来了。我高中毕业后安排在学校做教师,上班第一天几个哥们就一起约到饭店去庆祝,点了几瓶青梅气酒,我开瓶时操作不当,瓶盖子飞在左眼上,当晚就住进了医院,医生见我年纪轻,可能估计是打架造成的,也就没有说实话了,说这只眼睛怕是保不住了。大姐听闻我眼睛打坏了,她是哭着找到我病房的,这时我能体会到的就是亲情,能看到的就是大姐对家人最真诚的爱。我住了一周的院也就恢复无大碍了,时间不长就迎来了我20岁的生日,父母还在船队上,家中只有我和大姐,为此大姐特地买来了菜为我请客,我把高中要好的同学和学校的几个年轻老师请过来热闹了一番,大姐的家就象我的家一般。我在学校任教期间也都是有事没事地要来大姐家跑跑,看得出她每次见到我都很开心,在我们船家子弟中老师这份工作是一份为家人挣面子的工作。在船厂职工宿舍区,大姐多多少少也为有一个做老师的弟弟而感到些许的自豪。
1986年,我24岁,大约在五月初,有一天船队进港卸货,听家人说起父亲的身体情况,隐隐约约好象是什么不好的病,大姐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已成泪人一般。我知道情况不妙,父亲是一家人的主心骨,是家中的一棵大树,一家人多少年来都是在他的庇护下。我们对父亲都言听计从,除了亲情还有敬畏。大姐没什么文化,二哥张罗着为父亲检查身体,最后决定去南通肿瘤医院进行确诊。
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与家庭事务的分担上,大姐是一个永不知疲倦的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有几天几夜不睡的精力,但当听到父亲最终确诊为肺癌的时候,忙前忙后一直没得到好好休息的大姐突然昏倒在南通肿瘤医院的门诊楼前,我们一家人手忙脚乱地抬着大姐去急诊,谁也不知道她的病因,医生诊断后告诉我们:着急、惊吓所致!
父亲于当年冬天去世,一棵大树轰然倒地,最伤心的除了母亲外就是大姐,在她痛不欲生的哭诉中我们都明了她心中的苦楚:家中兄弟姐妹七个,作为大姐的她最吃苦,一天学校没进,靠单位办的扫盲班学了几个字,工作前就一直在水上帮父母撑船、拉纤,拿到工分后自己的收入也都用来养家,工作后还一直负担着最小的妹妹,硬是靠自己的一双手省吃俭用建起了自己的小家,她没有对父亲的责怪和埋怨,更能理解作为家长的艰难,而父亲辛劳一生还没到退休年龄就早逝了,没享到福,想到这些,大姐一直沉湎于悲痛之中,一边要帮助家中料理各种事宜,一面以泪洗面。
大丰的河口其实是指原新团乡的河口村,但随着以水上一村为中心的西河口地区的快速发展,周边先后有了学校、石灰厂、水泥厂,久而久之“西河口”便成了这一地区的特别地名。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原先水上船民慢慢得到了按人头分得的.土地,船民可申请在单位所属土地上按计划建房,大姐最先想到了建房,父母将自己的土地指标给了大姐,于是大姐便有了自己的三间平房,有了自己的房子后大姐将她婆婆接来照料,大姐夫弟兄五个,在家排行老六,大姐不仅仅对自己家人厚爱,对婆家人也一样厚待,最终,婆婆在她家养老送终。大姐先后照料了老人家20年。
时间过得太快,转眼间大姐的女儿也出嫁了。在南京举办婚礼时家里的弟妹们一个不缺全都参加了,这是大姐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但就在这前一段时间却也经历了一场惊险:一直在船厂小心谨慎的她在私家企业操作钻床时被钻床卷住了长发,眼看着头就跟着机器旋转进去了,大姐于是拚命地把头往后一拽,上面的头发连着头皮脱离了她的头。后来到医院去看她时我们不由得联想起那句“头掉了不过碗大个疤”的定义,在心痛不已的同时也庆幸大姐能死里逃生,从此她便戴上了假发。
母亲年纪越来越大,母亲于2003年因十二指肠穿孔动手术后就一年不如一年,这以后家庭中的一切大小事务大家也都得听大姐的安排,遇事要跟她商量。
2010年,母亲的耳朵已经听力很低了,做事也变成越来越莫名其妙,冬天衣服多,自己的棉裤常掉下来也不知道提,到菜场买菜也常常不知道要人家找零钱,好在人家都熟悉她,不忍心欺骗一个头脑不行的老太太。更奇怪的是母亲一遇到我就会在我面前数落着大姐的各种不是:
“你这大姐心太黑,电瓶车都能开到我家来充电,一充就充一夜。我几袋子大米被她偷走了,油也被她倒了大半瓶子去,家里的钱一不注意就被她偷走了。”大姐在母亲的眼里俨然成了一个家贼。
母亲不仅仅是在我面前说,还会在其他邻里面前说,大家都知道大姐偷母亲的钱、偷母亲的家私,后来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翻出了母亲存放在香烟盒里的一千多元钱,大姐激动得流泪了,她说:总算是找到了,要不然还真以为是我拿了她的钱的呢。多数人知道妈妈有了老年痴呆,也会有少数人不明就里啊。大姐那时已经办了退休手续,但因为她的电焊技术好,人家私人企业争着请她去,工资也不低,二百元一天。大姐不管再忙,下班也要到母亲这里陪她,随便母亲如何说她、如何坏她的名声,她只能是一个人偷偷地哭泣,也不会弃母亲于不顾,再多的委屈也是一个人自己独自承受着。再后来母亲不仅仅是在背后说大姐的不好了,更是当面不是哭便是找到顺手的东西就打来,受尽了委屈的大姐依然如故,还是一有空就来陪母亲,因为母亲已经不能自理了,大姐不在的时候母亲连饭已吃不到嘴了,也分不清食物存放的时间,分不清食物是否变质,家里人轮流照看着,大姐还是去得最多。
2011年春节后,大家觉得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得为母亲最后几年的时光有个合适的安排,最终商定将母亲送到福利院。
由于母亲大脑不能自己控制,福利院最终也呆不住了,我们只能将母亲接回她自己的住处,由刚办了退休手续的三姐专职照料,这一来就是四年时间。每年有几个特定的节日和特定的日子,一切还得按母亲健康时常做的形式由大姐负责操办着,平常一有时间大姐就来帮母亲洗澡、擦身、喂母亲吃饭,直到去年下半年,大姐把母亲又从三姐家接了过来照料,这是最后的两个月,母亲时常会出现一些状况,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她也不会打电话叫我们。
母亲一直拖到父亲忌日这一天去世,二老于同一个日子离开这个世界,在一切事宜都完成之后,大姐一个人昏倒在厨房的灶边,大家七手八脚地弄醒她之后让她一人人痛痛快快地哭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知道她有一肚子的委屈。
父母都走了,兄弟姐妹们在大姐的召唤下还时常聚到妈妈的老房子里,她自己也隔三差五地来睡几晚,打电话叫我下班顺道去吃饭,知道我喜爱吃鱼,在我吃好饭回家时她会将烧好已经冰起来的鱼放在我车上,让我带回家吃。看着她盘子里的鱼,一种母爱般的慈爱令我动容,我的泪在眼眶中开始打转。
人家说长兄如父,我要说姐大如母,大姐为我们所做的每一点小事都是母亲身前为我们做的,有大姐坚守着母亲的家,我们一大家的人还会跟以前一样团聚起一起,还如母亲在时一样感受到大家庭的温馨。